11月30日晚,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,日本欧亚基金会(Eurasia Foundation)资助的2021年“亚洲和欧洲:全球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”课程系列讲座第十二讲——“‘东方主义’之前:十六世纪欧洲旅行书写中的亚洲形象与世界意识”于线上成功举行。本次讲座由福建师范大学周云龙教授主讲,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叶向阳副教授主持。

讲座伊始,周云龙教授以爱德华·萨义德(EdwardSaid,1935-)在《东方学》(Orientalism: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,1978)中所提出的“东方主义”为出发点,解释了何谓“东方主义之前”。周云龙教授首先说明,他探讨的对象时间在十六世纪,在萨义德意义上的“东方主义”之前。其次,此时期,由于航海技术、保密政策等因素的阻碍,旅行书写具有“异想天开、光怪陆离”的鲜明特征。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,则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认知冲击,不能简单实用“东方主义”的批评框架。第三,十六世纪作为“地理大发现”的世纪,在欧洲跨文化旅行书写中出现大量不同文明之间互看互释的内容,同时形成了以全球为构架的世界意识。因此,对十六世纪欧洲旅行书写中的亚洲形象研究,不必刻意排斥“东方主义”批评,但更需要站在“东方主义之前”的视角,才能有效回应这一时代的核心问题:欧洲旅行书写中的亚洲形象如何参与其世界意识的形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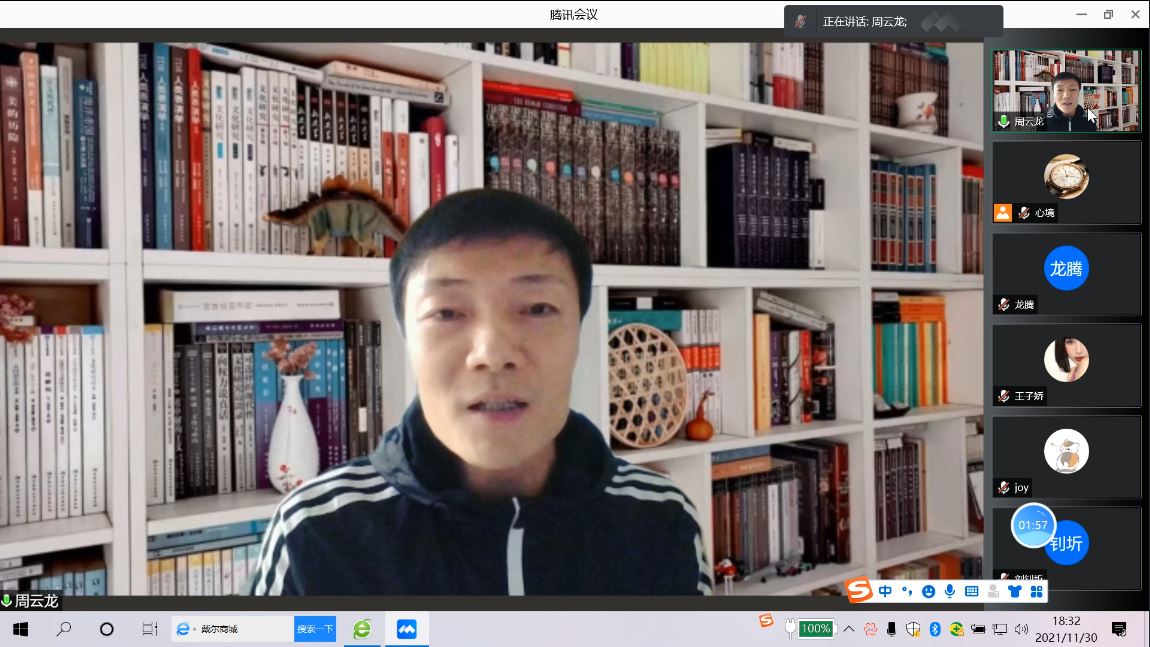
随后,周云龙教授对“旅行书写”和“亚洲”两个关键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。周云龙教授认为,“旅行书写”不完全等于游记,它是一种开放、无边界的文类,是一种“反文类的文类”,所以区分纪实或虚构在此已经没有意义,任何类型的文本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隐喻或欲望投射。在十六世纪欧洲旅行书写中出现的“亚洲”,不等于早期近代亚洲各个区域或帝国的物理实体的相加。其根本原因还不在于“亚洲”地理边界持续地变动不居,以及早期近代欧洲的“亚洲”概念的混沌含糊,而是因为,亚洲在这项研究中不是一个现实的、统一的地理概念,而是一个存在于欧洲大众的观念世界中的文化的、政治的心理概念。
在此前提下,周云龙教授对几部重要的旅行书写著作,包括多默·皮列士的《东方志:从红海到中国》、路易斯·德·卡蒙斯的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》、费尔南·门德斯·品托的《旅行记》,以及莎士比亚的《考利欧雷诺斯》进行分析和介绍,并以莎翁剧中的主人公马尔舍斯为例,指出马尔舍斯“为了追寻自我,必须远走他乡”,在“发现”世界的同时也在“发现”并确证自我,是十六世纪欧洲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隐喻。这种“别处另有世界在”的态度,周云龙教授视之为“地理大发现时代”欧洲的文化政治无意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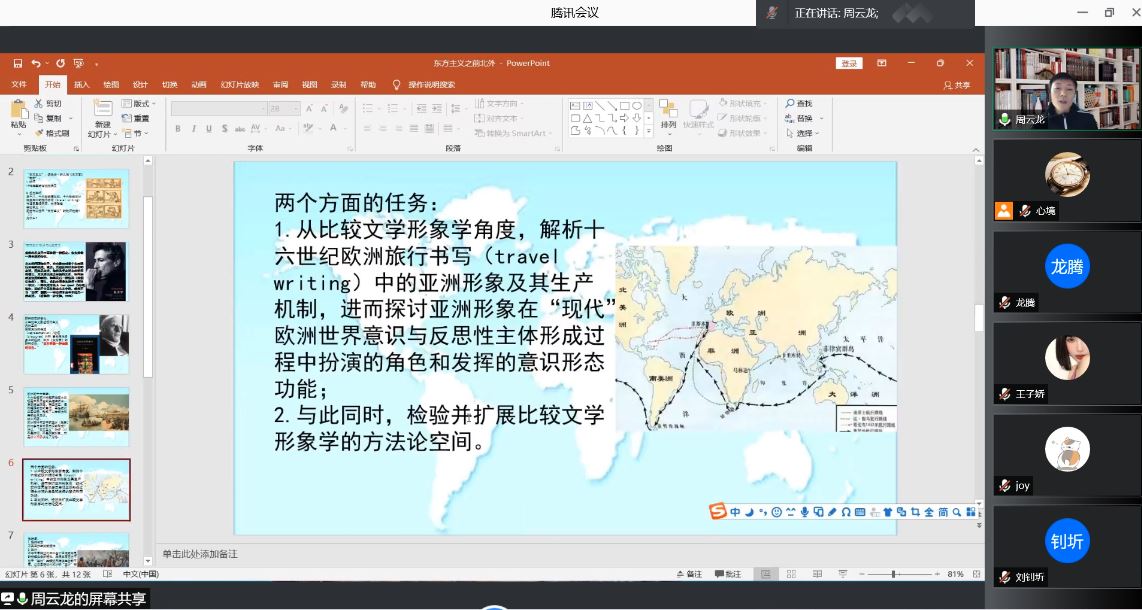
讲座结束后,周云龙教授总结了他自己的这项研究:以多样的途径切入不同文本,以相同的哲学前提和话语分析进行解读,以“世界意识的形成”作为问题意识贯穿其中。周云龙教授认为,文本是分散的,各有各的关怀,进入的途径也应该是不同的,但“世界意识”作为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,使得这些文本得以呼应、连缀。
讲座最后,叶向阳老师进行了点评,他指出,周云龙教授通过更为复杂的理论和更加丰富的文本,作为其研究的方法,超越了学术界讨论西方形象问题的固有理论框架,也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“游记文学”的范围。在互动环节,我院师生积极提问,周云龙教授一一做了详细解答。在师生间热烈的讨论中,本次讲座圆满结束。
(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王子娇供稿)